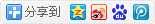直指天空的两根三叉型钢柱,曾经嵌在世贸北塔的钢架中,目睹了十年前撕心裂肺的灾难;一段已经锈迹斑斑的灰黑色防水墙,仍然矗立在十年前的老地方,是双子塔劫后留下的唯一原封不动的骨血;一棵十年前被烧焦的豆梨树,驱干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如今却已经重新枝繁叶茂。
这个被称作零点废墟的地方显得充满了玄机,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伤痛还是希望,是死亡还是新生,或是什么都有,或是什么都没有,也许都不过是你自己的心情和体验的投射。刚刚落成的“9·11”纪念馆单凭名字就足以与这些历史遗存浑然一体——“倒映虚空”。
在“9·11”十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幕的纪念馆占地8英亩,是零点废墟重建的庞杂工程中最先完工和对公众开放的项目。沿着青石路,穿过400多棵白橡斑驳的树影,大地在眼前洞开,两个200英尺见方、30英尺高的水池被包裹在飞流直下的人工瀑布中,水流在池底汇集平缓如镜,之后再落入15英尺深的池眼里。水池的四周的短墙支起黑褐色的铜匾,匾上满满刻着是死难者的姓名,2983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触起来只剩指尖的冰冷(死难者姓名包括飞机乘客、1993年世贸0案中的死者和牺牲的救援人员)。
对他们这里是终点,但谁能说这里不是一个新的起点呢?两方水池正坐落在世贸大楼的地基之上,双塔不在,四周绿树蓝天,新的住宅和办公楼正拔地而起,起重机高架,混凝土机轰鸣,人们踌躇满志,行色匆匆。纽约不再是满心伤痛,零点废墟不再是满目疮痍,“9·11”纪念馆方案几经修改与当年的蓝图已经不同,而它的设计师们在经历了这个里程碑式的工程磨砺之后也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自己。

所有的变化都倒映在两方空池满水之中。
用图纸疗伤
位于曼哈顿苏豪区的汉德建筑公司的办公室基本上只有一种色调——白。厂房一样的工作室大得一眼望不到头。这种简洁似乎正对了公司合伙董事麦克·阿拉德的胃口,至少在别人的眼中,他的作品是简洁主义的典型。当然,至今他为世人所知的作品其实只有一件——“9·11”纪念馆。
那天早上,阿拉德正在自己位于曼哈顿东村的公寓里洗漱,从广播新闻中听到一架飞机撞到了世贸北塔,抱着看热闹的好奇,他跑上楼顶,正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我意识到这绝不是事故这么简单。”在下城金融区工作的妻子这时已经到了公司。阿拉德骑上自行车向妻子的公司冲去,找到妻子后两人一起往家走。刚走过了两条街,南塔就倒了,快到家时,北塔也化为灰烬。
“9·11”刚过不久,他就开始在纸上勾勒纪念馆的图案,那时纪念馆方案的征集竞赛还没开始筹划。“开始设计时根本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把这个当成是一种思考和疗伤的方式,就好像有人练瑜伽,有人打坐,建筑师是用图纸来思考的。”阿拉德说。
之后他离开了KPX,转到纽约市房屋局工作,开始设计政府楼附近的警察局。他心中的纪念馆方案也在不断演进,从最初不切实际的在哈德逊河河面上切出两个方洞,到在世贸双子楼的地基上打出两个瀑布水池。这成了2003年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LMDC)在世界范围内征集“9·11”纪念馆设计方案时,阿拉德提交的定稿。
经过5个多月的初选,阿拉德的“倒映虚空”凭着在双子塔地基上挖掘深意的独特构思,从应征的5201件方案中脱颖而出,被列在进入决赛的8件方案之中。但最终的胜出并非水到渠成,这8件方案个个别具匠心,而评委们对阿拉德的方案也并不是完全满意。他们喜欢他的水池,但认为水池周围的广场显得太单调,不能达到集纪念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目的,他们建议他找一个园林设计师做搭档,把方案修改后再参加决赛。在评委会推荐的人选中,阿拉德选中了著名的彼得·沃克。
沃克的树
事实上,沃克自己也提交了一份以树和嵌有死难者姓名的玻璃纪念碑为主体的设计方案,但没有进入决赛。“我接到麦克的电话时已经上网看过进入决赛的8个方案,所有入选的设计者都是无名后辈,但只有麦克的方案让我觉得我可以有用武之地。”79岁的沃克说。
沃克的补充设计让阿拉德的方案如虎添翼,最终夺魁,沃克的400棵橡树也得以从图纸上走上了纪念馆广场。
比树木的挑选更复杂的是保养和灌溉。沃克说,在纽约这样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树木的生长期一般只有7年,而纪念馆广场上的树又是建在地下纪念馆的房顶上,更会影响发育,如果这些树七八年后都一起停止生长,它们将成为纪念馆的一个败笔。
为了让这些树有至少100年的寿命,设计者必须建造一个复杂的营养和灌溉机制。“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绿色工程,将来我可能会写本书专门讲这些树的故事。”沃克说。
阿拉德的崩溃
如果说“9·11”纪念馆从设计技术上已经足够纷繁庞杂,比这些更难以驾驭的却是围绕工程展开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同利益团体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经费、安全等客观条件对纪念馆建设的限制,妥协和让步似乎成了纪念馆工程能否继续的关键,而这对于性格狂放唯我独尊的设计师们,特别是年轻气盛的主设计师阿拉德来说,又是最难做到的。

2004年纪念馆方案征集比赛进行最后角逐的时候,阿拉德只有34岁,他之前独立设计过的工程也只有一两个警察局,在评审过程中,这似乎帮了阿拉德。据说“倒映虚空”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源于评委之一——林徽因的侄女、著名建筑师林璎的力保,除了两人在设计风格上的近似,更因为当年林璎设计世界闻名的越战纪念碑时和阿拉德一样也是无名小卒,遇到了伯乐才一举成名。
在最初的几年中,阿拉德几乎都跟其他参与工程的人吵了个遍,包括资深建筑师戴维斯·邦德、麦克斯·邦德(已故)、零点废墟重建总工程设计师李柏斯坎,从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9·11基金会、纽新海港局到纽约州长办公室,所有人都知道阿拉德有个坏脾气,他固执己见又盛气凌人。
名字的排列方法
设计师向死难者家属发出邀请,请他们提出自己亲人的名字应当与谁排在一起的建议,之后阿拉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把名字排好了,家属们提出的1200条建议全部得到了满足。
“当你看那些名字的时候,他们好像是随便排列的,但对于知道其中故事的人,他们又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一个女孩的父亲在世贸倒塌时丧生,而她最好的朋友又是宾州坠毁的那架飞机上的乘务员,只有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才能显示出‘9·11’对生命的巨大摧残。”阿拉德说。

十年间,纽约虽然痛楚仍在,却慢慢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沃克的建筑公司扩大了规模,“9·11”纪念馆让他更负盛名。“本来园林设计不大被人们重视,可一旦你上了早新闻的访谈节目,一切都不同了。”沃克说。对于突如其来的名气,阿拉德似乎反而更平淡些:“我生长在外交官家庭,在公众目光下生活并不是新鲜事。”
阿拉德如今是3个孩子的父亲,老大奈迪今年8岁了。“虚空池”试水的那天,阿拉德带儿子到了现场,小家伙对建筑已经表现出天分和兴趣,但对于发生在他出世之前的“9·11”,他仍然似懂非懂。“他这个年龄还很难理解死亡。”

下一代人是否能够远离劫难,在和平的空气中幸福的长大?阿拉德不能肯定,但现在,他至少懂得教孩子们如何应对:“也许战火还是会发生,有些生命还是会无谓地死去,但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劫难中坚守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不让它改变我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