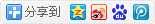遥望公元759年,崎岖蜿蜒的蜀道上,一位衣衫褴褛面色饥黄头发花白的诗人带领着全家老小,从狼烟四起的关中一路跋山涉水,向着美丽富饶的成都缓缓走来……
“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于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午后,在充满诗意的浣花溪畔,我怀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拜谒了这位终生颠沛流离及至穷困潦倒的诗人,以及曾给他短暂停歇的草堂。
最早认识杜甫,当然来源于唐诗。
想必和很多中国孩子一样,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我便被父母强迫着背诵古诗,其中自然少不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也离不得杜甫的“两只黄鹂鸣翠柳”。只是李白的月光泛着思乡的清冷,杜甫的黄鹂与翠柳组合则是一首春意盎然的小曲,一幅湿意淋漓的水彩画。
想象中的草堂应该是充满着乡野气息之所在,芳草萋萋,竹影摇曳,绿野仙踪,大有些许遗世独立的况味。当然,这毕竟只是想象。当我抛开尘世的繁华和嘈杂,一脚踏进草堂大门,闯入眼帘的,首先是一片湿漉漉的幽然而纯净的绿。轻风拂过,那绿仿佛在流动,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予人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和清凉,俨然一首有声有色的诗。
许是下雨的缘故,偌大个园子游人稀少,雨粒轻落在竹林和小径上,一如诗人苦涩里那一抹淡淡的微笑——翻山越岭,为避战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成都亲朋的资助下落得一处立足之地。茅屋何足惜,草堂不寒酸。“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这个命运多舛的诗人,似乎可以在此稍稍歇口气,安顿一下那颗操劳、疲惫的心了。
穿门过桥,绕过影壁,便是梅林后的大廨。腊梅刚谢,空留若有若无的清芬。大廨间矗立着一尊诗人铜像:双膝跪立船头,瘦骨嶙峋,愁容满面,那一袭暗色长衫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刮走……中年之后,他似乎从未快乐过,或者说从未真正舒心地笑一回。纵使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短暂飞扬和酒醉般的狂癫,那也是瞬间梦花开落,笑里含泪,泣中带伤!
草堂的主厅叫诗史堂,端放着一尊诗人的半身像:依然是微蹙双眉,愁颜不展,目光中透露出苦思忧伤。塑像两侧楹柱上悬有一副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系川籍伟人朱德的手书。堂内东西两侧分别是杜甫和李白的雕像。这两位诗歌史上惺惺相惜的大家,虽然性情和创作风格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感情真挚的好朋友。他们相互仰慕、推崇备至的唱和一时传为佳话。而命运就这样离奇:李白出身商贾之家,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祖父时迁徙到巴尔喀什湖畔的碎叶城,到父亲辈上又再度搬迁至四川江油。从此,他的命运和天性的形成便与川人川性密不可分。也可以说,蜀地的秀美山水与丰富人文濡染了他,他的诗歌与人品的飘逸、放达和不染尘埃,与四川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杜甫出身没落官宦家庭,祖父杜审言早在武则天时就是著名的诗人,他的家世和教养决定了他将按照儒家的理想轨迹做人处世,后来为了功名和理想而“朝扣富儿门,暮随飞马尘”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同样有着建功立业的梦想,有别的是,杜甫走的是科举功名之途,李白不屑于此,靠的是自己显赫的诗名与人气。虽然他们都在各自的努力下得到一定的赏识和重视,但最后还是流落江湖,贫病交加:一个病死于赦免的路上,一个吟叹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同样病死在湘江的一条渔船上。他们的命运给人许多思考,令人为之嘘唏,扼腕!
出了诗史堂便是柴门,也即是诗人常常提到的“蓬门”。“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颠簸的诗人在苦难中也会发现柴门上的溶溶月色,是否恰好温热了用来下酒?“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哦,那是久不相见的友人和欣欣然的花草带来春风的暖意……俯仰吟啸间,好雨知时而来,白鹭翩然而去。季节更替中,古老的黄桷树正在透绿,柴门上的爬墙虎悄然返青,并慢慢伸展开腿脚…
沿竹林小径往前,除了跫音,便是雨声。幽暗中听雨,似吟哦,又似叹息,本身就有一种凉润的诗意。信步向前,不觉倾斜的竹枝勾勒出一幅豁然开朗的画面:几丛高大的南国芭蕉丰硕颀长,临水照影;那水,漫漶着一弯碧绿,微风里漾起缕缕薄薄的雾气……不用说,这就是浣花溪。
浣花溪,一个似有流水淙淙、花蕊飘香的美妙地名。
嘴里轻声默念着这个地名时,仿佛在柔声念叨着一位心仪的女子——西施浣纱?貂蝉拜月?玉环羞花?还是这芙蓉城里的女才子薛涛正施施然巧手亲制桃花笺?如此曼妙的地名不知是谁起的,竟会引发这么多的浮想联翩。转念一想,一千多年前,流离颠沛至此的大诗人,可否也是因为这“浣花溪”的芳名而要在此诗意栖居下来,建一座草堂,以期会那冥冥中的清芬呢?
几排竹篱,几方矮墙,为漂泊的诗人构筑了一处宁静的家园,让他的失落跌宕的心情有了短暂的安慰。彼时正值岁末,和北方冬天的萧瑟正好相反,满街的绿树红花令锦官城的年景更加温暖而热闹,尤其是歌舞升平的蜀中气象与中原北土上战争带来的硝烟和饥馑形成巨大反差。在这潺潺流水的浣花溪畔,在这活泼泼四周充溢着田园气息和居家温馨的草堂里,他一反曾经的愤世嫉俗和苦难阴郁,抬眼看见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情境;在秉烛夜读的窗口,他侧耳听见了“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的温情;他已经很平和地感受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旖旎;他甚至精神一振,江畔独步寻花,忘情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了!
诗人本好游,不光李白,杜甫亦然。客居成都,自然少不了拜谒三国故都武侯祠。那祠中森森古柏和树上嘤嘤黄鹂,无法不让他慨叹一代贤臣诸葛孔明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凉。琴台路,曾经发生过才子佳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凤求凰”之浪漫私奔之地,其实距离浣花溪并不远,顺流而下,不知道诗人邂逅的是蒹葭苍茫野花缠绕呢,抑或文君动人的笑靥历历再现?
许是天府之国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令诗人在成都期间,满怀着罕见的温情与细腻的笔触,传神地描绘着成都的风光物态与蜀地的风土人情。这个寓居他乡的人每天以赤子般的爱怜,一一敏感着成都的日夜、成都的雨滴、成都的花草怡情,成都的闲适温润:草堂盖好了,他欣然提笔写《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登楼望远了,他即景抒怀:“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友人来访了,他殷殷迎送:“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甚至和周边的村农相处甚好,人家的樱桃熟了,采摘一篮送过来,他也以诗相记:“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老,心境却胜过流离失所时的任何时分。也许,较之于代表作的《三吏》《三别》所发出的悲苦呐喊,这些诗情画意情调别致的小诗,难以控诉当时朝廷的黑暗与民众的疾苦,但类似于“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和“一行白鹭上青天”等清丽景象,仍不失为一代大家留在人世的艺术瑰宝,遥远的绝响一般,回荡在天地苍穹之间。
如今,诗人已去,浣花溪千古留名。空寂的石阶上,草绿苔青,泛着岁月年轮的光泽;浣花溪的清流里,水藻漂游,印记着逝者如斯的伤痕。目光所及,耳畔所闻,伸手所触,无不是诗人苦难中的不屈,孤清时的超脱,贫寒不改其志的人格,以及无可比拟的美好诗篇。
和工部祠与大雅堂的巍然厚重不同,茅屋简朴得叫人叹息。尽管心里早有准备,毕竟中学时代就熟悉了那首著名的诗歌所述,但那是臆想中的,戏剧化的。真正的站在雨丝寒凉的屋檐之下,纵然屋后溪水环绕,门前古树婆娑,我,依然心里发酸,不忍卒睹。
陈设简陋的茅屋内,光线幽暗。因诗人是北方人的缘故吧,卧室里的床看上去宽大结实,很像北方的土炕。诗人儿子的小屋更是逼仄,阴暗。而被称作厨房的后间,则布置了灶台、水缸、石臼、石磨盘等日常生活的器具。抚摸着冰凉的灶台,遥想诗人饥寒交迫食不果腹时,那种“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的局促、凄惶,不禁百感交集——如此这般来苦熬度日,怕是世界上最贫穷最悲惨却也最伟大的诗人了!
狭小的书房,开着同样狭小的木棂窗户。一桌、一椅、一只简陋的书架,可能这里也常兼做诗人会友的缘故吧,另外加了一只矮小的几案。竹制的笔筒里插着一支毛笔,旁边是一本落满了灰尘的书卷——在如此孤寂的环境中,我能体会出诗人当年的清苦和诗味的幸福:在那些桃花灼灼、蛙声四起的春夜,饱含着成都平原特有水气的和风,从浣花溪的水面上轻轻吹拂过来,诗人独坐在一盏荧荧如豆的油灯下,一边磨墨,一边思忖着令他焦虑忧心的时事,那些千古名句便在心潮滚滚中蜂拥而来……
可惜,茅屋终究是因陋就简,一千多年前的浣花溪畔还是无遮少挡的空旷原野,因而他的这个新家常常遭受到大风的袭击。那一个秋天,阴霾密布中,呼啸的大风将屋顶上的茅草几乎吹了个一干二净,也因此引发了那一首深沉悲切的煌煌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个人的伤痛和绝望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这种呐喊,今天听起来依然铿锵有力,振聋发聩。我想,这大约就是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诗圣的缘由吧。因为,没有生活、胸襟和生命的诗是苍白的,注定只能昙花一现,瞬即凋零。杜甫的诗推己及人,胸中装的是天下苍生,是生活最底层的呐喊和抗争,唯此,他的诗才具有永久的魅力和感人至深的力量。
苦难的磨砺,颠簸的艰辛,报国无门中,只有借着诗歌来抒发着自己的失意,但又不被失意的情绪吞噬。悲苦难抑的心境和愤世嫉俗的个性给了他一支匕首似的诗笔,为我们展现着唐朝末年纷纷乱世下的惨淡民生,为我们泣诉着故土难离家园难归的无奈痛心,以及诗人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坎坷一生,终不得志,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留下了一颗高贵的心!
轻轻走着,看着,竟然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诗人还在这里,还生活在这座成都人特意为他营造的虽然简朴却异常幽雅的园子里。他的呼吸,他的生命,连同他的书桌,他的床榻,他的茅屋,他的诗篇,在此或安憩,或轻扬,以至与日月同辉。
温馨提示: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是唐代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从正门开始,依次是大庙、诗史堂、柴门、工部祠。其中大庙、柴门是杜诗中提到的草堂原有建筑,诗史堂正中是杜甫立像,堂内陈列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联、匾额。工部祠内供奉有杜甫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