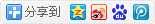余神往上海苏州之江南风物久矣!
5月1日晚上至5月4日,余与内人及众驴友45人一道,报名报业旅行社,同游上海、苏州、同里、木渎四地,旅途之中颇多见闻感慨,今聊散记之,且自娱也,并与网络众友共同回顾。
5月2日,苏州,天气晴间多云,傍晚有阵雨。
5月1日夜7时整,四地游的45名驴友及报业旅行社领队等共49人自青岛出发,跋涉近千公里,2日晨抵苏。早餐后游寒山寺、狮子林。午餐就于苏州商贾云集之地观前街,食什锦汤、罗汉排骨、苏州炒饭,午餐后游苏州盘门三景,夜宿于无锡远郊之某宾馆——据同行之驴友称,该宾馆当夜之一楼有蛇出没。不唯如此,该宾馆之牙具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牙刷甫一入口,未经捣得两下,其柄即如蒙牛随变雪糕一样松软弯曲变形矣!
寒山寺。
就象游北京不能不游故宫和长城一样,游苏州似乎也不能不提到寒山寺。虽然这个寒山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寺庙相比,几乎拥有相同的草胎泥塑神像、佛塔、宝殿、讲经堂等等建筑类型,其内庭和外观也几乎毫无二致,但它仍然因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有异于中国其他地方的同跻。张继的这首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情趣、意境悠远并含有某种浓厚的佛教禅宗韵味的诗句,其氛围竟使寒山寺盛名远播达近千年之久,真的是做到了寺以诗名。而到了近代,更因为林则徐、董其昌以及国学大师俞樾等人的题跋、唐寅、文征明、康有为等人的手书而名声大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余游览寒山寺之心亦久矣。而如今的寒山寺已不再位于姑苏城外,想听那寒山寺钟声的客人也不再仅限于居住在孤零零的客船上。对于游客们来说,这方便固然是方便了许多,但要领略诗、寺、钟声、客船合而为一的意境似乎也因此而减少了许多,毕竟,寒山寺带给人们的想象也会因此而大打了折扣。
但本次游苏,未曾预料的竟然多了些许郁闷,至最后,更加生出许多愤怒,以至于几乎彻底打消续游之念,只是走马观花而已。且不说寒山寺接纳游客因经济发展之故致使日日为盛,但看五一长假即极其火暴。运河上江村桥和枫桥观光人潮起潮落,人头如炽,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发作,殊无半点“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意境。而所谓的“夜半钟声到客船”者,则更是无从说起,寒山寺的大钟被一干能够出得起5块钱的好事者、无聊客一通乱锤,大煞风景之极矣。
及至进至二进厅门,见院中赫然耸立巨树数株,而标牌上注明,此树全为名樵山(?)者之倭人所手栽,当真另人惊诧莫名。据我所知,虽然佛教禅宗自唐代即东传倭邦,倭人向佛教大乘教义之心甚盛,但是自从1895年、1931年、1937年、1938年的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事端以来,倭人之所谓信奉佛教的虚伪几乎在国人面前昭然若揭,而国人也对倭人之是否真的有所谓的向善之念绝不相信。游览结束后我曾查阅苏州一些地方史料,内中记载使人发指之处比比皆是:
“八一三事变后三日,倭人即始轰炸苏州,苏州之大中旅社首遭其祸,民房毁三十多户,居民死三四十人……徐光斗一家三口尽遭屠戮,铜锡店掌柜媳妇身怀六甲,被炸身首分离。”
“(1937年)11月19日,倭寇海劳原所部攻入苏州,阊门外马路至京剧场、真光电影院两侧商店七八百家,可怜一炬,尽成焦土。自接驾桥、东西中市至阊门石路,日夜火光烛天。……三日内被倭寇屠杀者逾千,(倭寇)旬日后方始封刀。”
“功德林老板何桂芳组织掩埋队者九,分赴九门,十日内共掩埋尸体2870具,四乡被杀者5000余具,尸首腕上手表集二箩筐,河中浮尸连接数里。”
“(1939年)吴江县被倭人杀7296人,毁屋8407间。”
等等诸语。翻阅此段历史,内“惨祸”、“屠城”、“血洗”之语随处可见。而今寒山寺内竟然植倭人手树,不只盗窃愚民香火,还为我国人日夜拍照存念,以作为”到此一游”之谈资,此实为天人所共愤。而寒山寺尤其将与所谓的倭人合作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之言行视为荣光,则更为可恨,此实在是本次出游所见之大耻辱。余不堪目睹该匪夷所思之怪现状,故匆匆一观寒山寺之普明宝塔后,即掩面奔出,不复回顾矣。
按:寒山寺之普明宝塔位于寒山寺后,高逾42米,五级四层,楼阁式仿唐朝佛塔,于清朝末年太平天国乱时,为太平军焚毁,1995年重建。另人遗憾的是,焚毁普明宝塔的始作俑者竟然因种种原因未见史料记载,似乎有人也在故意为太平军者讳言,对太平军的种种劣迹以及其反文化、反人类、反传统之邪教本质、乖谬行径避而不谈,不为后人所道,以至于后人对此段历史竞致一无所知,——余尝闻同行之驴友提及,竟然以为焚毁普明宝塔者为文革之红卫兵,殊不知文革固然是反文化之革命,而太平天国之荒诞怪戾,更有过文革而无不及也——呜呼,不哀寒山寺普明宝塔之被毁,而哀毁塔者之不为后人所知也!
狮子林。
狮子林无疑是中国南方园林景观及假山造景方法的代表之一。游览之始,导游即将苏州园林之假山堆砌的审美精髓知会众驴友,谓之“漏、透、瘦”云云。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元末名僧天如禅师维则的弟子“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师。”因园内“林有竹万固,竹下多怪石,状如狻猊(狮子)者”;又因天如禅师维则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普应国师中峰,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师子林”、“狮子林”。后来陆续建设完善的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之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遂而盛名于世,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
元代流传至今的狮子林假山,群峰起伏,气势雄浑,奇峰怪石,玲珑剔透。据说假山群共有九条路线,21个洞口。横向极尽迂回曲折,竖向力求回环起伏。游人穿洞,左右盘旋,时而登峰巅,时而沉落谷底,仰观满目迭嶂,俯视四面坡差,或平缓,或险隘,带来一种恍惚迷离的神秘趣味。“对面石势阴,回头路忽通。如穿九曲珠,旋绕势嵌空。如逢八阵图,变化形无穷。故路忘出入,新术迷西东。同游偶分散,音闻人不逢。变幻开地脉,神妙夺天工。”“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当真是狮子林的真实写照。据史载,1703年2月11日康熙皇帝南巡、狮子林赐额“狮林寺”后,乾隆皇帝六游狮子林,先后赐“镜智圆照”、“画禅寺”及现存“真趣”等匾额。乾隆还下令在北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内仿建了两座狮子林。可见当年帝皇也对狮子林情有独钟。当地的俗话称,“苏州园林甲江南,狮子林假山迷宫甲园林”,当日一看,果不其然。
狮子林一游唯一不足处,是假山上屡屡为粗俗之辈攀爬,做猴子状,做极其NB状,更做出种种与赏玩园林及假山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之怪诞动作姿势,以做拍照留念,真可称得上是全国各地姿势,在此一览无余也。
当然,狮子林终究还不能等同于苏州之拙政园。
出狮子林,乘车趋午间休息地。车辆转弯时,不经意间,竟见拙政园,其侧乃姑苏名妓柳如是故居,再侧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之忠王府,三座园子汇粹一地,其情状当真意味深长。面对此景,竟无法下车一览,实在遗憾。
盘门三景。
苏州一日,午餐后游盘门三景。
盘门系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奉吴王阖闾命修建姑苏城时,建造的八座水陆城门之一,所谓的“龙蟠水陆”,当真是道尽了一方形胜。但在今天看来,盘门的全部游览价值仅限于其春秋时期的军事用途,可观赏的文化色彩极其微弱。况且,盘门自修建完成,即因其风水问题,始终处于偏僻之地,即使到了清代,把盘门一带开放为外国(主要是倭人)租界,也未能带动起此处的繁荣,是向来被当地人称做是“冷水青汤之地”的。当年,倭人租借此地时,当地的车夫甚至宁可不挣钱,也不愿意拉倭人到盘门一带,这固然有苏州人讨厌倭人的风骨在,而盘门的偏僻也由此可想而知。在游览盘门的路上,我在想,在苏州这水陆萦回之地,世道承平时,商旅固然气逼阊门,而在兵荒马乱时,强人又道出太湖,窜没于胥门,而这两者,似乎也都与盘门无缘,这里被称为“冷水盘门”,恐怕也真是名副其实的。这里在今日竟然被干成旅游景点,人气鼎盛,却是姑苏人始料未及的,而对于一些渴望领略姑苏文化的人们看来,盘门也无非是平地起景,殊无可看之处。
苏州一日,抱憾者数。而尤其遗憾的是,未能亲自到我国清朝的国学大师俞樾的曲园一游。俞樾自号曲园,园以人名,故园也称曲园。俞樾于1850年30岁时曾进京应礼部考试,当时的礼部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曾国藩,给俞樾的诗题是“澹烟疏雨落花天”,而俞樾依题而做,起首即以“花落春仍在”一句博得曾文正公的激赏,曾国藩认为此句取意积极,显示出作者俞樾的名位未可限量。但最后俞樾的仕途似乎并不如曾国藩所预测的那样顺畅,后来俞樾在仕途失意后,就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全部镶嵌在曲园的花、石、堂、轩之间,曲园内修有“春在堂”,并以老子“曲而全”的哲学意味,名园曰“曲园”。此次赴苏,未能至曲园一观,瞻仰前辈风采,揣摩园主心境,甚为可惜。
当夜,宿无锡远郊。为解白日游览劳乏,品当地产三得利啤酒一瓶,大呼上当。次日与同行驴友发牢骚曰:“若论平生所饮之天下啤酒,青啤可当第一,燕京次之,尿属第三。而至于三得利啤酒者,比之尿尚有所不及也。”
5月3日,木渎,同里。天气中雨,阵雨。有时晴。
3日,众驴友自无锡远郊之偏僻宾馆出发,跋涉近百公里,抵苏州吴江县之木渎。早餐后游木渎之明清街,访严家花园。时近中午。遂趁午间奔赴同里,自同里刘家弄入同里之明清街。午餐就于同里,品味太湖之银鱼炒蛋、雪菜肉沫。真美味也。
木渎。
据导游事后对于之所以将众驴友发配之百里以外之无锡、而游览木渎、同里须来回奔波几近两百里、费时一小时许的解释,云称木渎原定宾馆当夜正值警方抓嫖扫黄被封,故临时调整住宿之地。而在到达木渎之后,细察该地,即对导游之解释倍生怀疑,所谓抓嫖、扫黄之说几近捏造,以该地之民风、人文环境及居住条件而言,抓嫖之事几乎绝无可能。
木渎位于江苏吴江县的远郊,为苏州、上海附近的著名文化古镇之一,不唯文化风气鼎盛,名人驻足、留香处极多,而且镇中的明清时代建筑遗留者亦很多,仅次于其附近的同里和浙江的乌镇。据当地人介绍,木渎是清代康熙皇帝三下江南、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每次都弃舟登陆的地方,可知木渎之秀美、风物之迷人。
在进入木渎明清街——严家花园沿途各风光点的入口处,立有牌楼一座,上书“东吴遗韵”,牌楼旁边的导游牌上,则标识出了这里的两个最能够代表东吴遗韵的观光景点“严家花园”和“榜眼府第”。根据当地的历史资料分析,这里也许确乎是最能够体现出东吴文化的地方所在。木渎镇地处苏州城西,太湖之滨,四周群山环抱,峰联岭属。灵岩、天平、狮山、七子、尧峰等吴中名山环如障列,苍翠悦人,是一个物富民丰,人杰地灵的"天然聚宝盆"。
作为一个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镇,木渎之名,相传为春秋时吴王阖闾败楚之后,大兴宫室,得越王勾践进贡之木,筑高台于姑苏山。因此项工程耗资巨大,“三年聚材,五年乃成。”木材积压在此地达三年之久,沟渎完全堵塞,谓之“木塞于渎”,木渎由此得名。而民间似乎可以更加放肆一些,关于“木塞于渎”的传说,认为是夫差为讨西施的欢心,特建馆娃宫于灵岩山,为美人游息之所。从导游图上看,现在灵岩山上的一些名称,似乎也仍在沿袭吴宫旧名,如吴王井、玩花池、西施洞等。馆娃宫所需木材也“木塞于渎”。而所谓的“馆娃”究竟是宫殿的名字还是一种类似于今人制作的名为“充气娃娃”的东西,本游者尚不得而知矣——玩笑!。
木渎历史可上溯吴越春秋,其中胥江、香溪均为吴越遗迹,文化蕴积深厚,名胜古迹遍布。境内除了山川林石之美,更有小桥流水之秀,古宅深巷之幽。镇上河道纵横,桥街相连,山塘老街则为乾隆御道,小镇人家或临街或枕河,粉墙黛瓦,重脊高檐,一派典型的水乡古镇风貌。而在余看来,整个木渎最为吸引游客、也最为导游者和商家券顾并能够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旅游资源及项目,则非古镇区互相毗连的深宅大院莫属,而这些深宅大院,又尤以严家花园、榜眼府第和古松园等私家花园为最。
严家花园。
严家花园又名羡园,集苏州园林之大成,为江南名园,园主人系当地的名门望族严氏家族。严家花园最早为乾隆年间苏州大名士(木渎人)、我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长寿诗人、著名诗选家沈德潜所建,那时候还叫做“灵岩山居”。道光八年,此园被木渎诗人钱端溪买下,取名“端园”。该园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其独特格局为江南诸多古镇中少有。清人王汝玉有诗赞其魅力曰“山近灵岩地最幽,香溪名胜足千秋”,实在不是虚言谬赞。1902年,木渎首富严国馨购下此园,由香山帮建筑大师姚承祖率巧匠重葺,更名“羡园”,又名“环翠山庄”,俗称“严家花园”。 花园占地十六亩,除中路三间五进住宅外,另有春夏秋冬四季小屋。园中几株古广玉兰冠幅宽广,浓荫蔽日,相传还是乾隆下江南夜宿沈宅的时候所栽下的。而楠木大厅尚贤堂、名士堂尤其气宇轩昂,江南罕见。清朝年间,木渎的榜眼冯桂芬(林则徐门下弟子,后入李鸿章幕府,为李之高级幕僚,清朝年间著名政论家,李鸿章之具有改革开放、振聋发聩的名言“此实中华民族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实出自冯桂芬之手),因官场失意,曾经寓居严家花园之名士堂。
提起严氏家族,在当地也许让人如雷贯耳,但外乡人如我辈之驴友者,听了这个家族的名字往往不知深浅、不知轻重、不以为然,似乎近于耳旁风。但严家实在是大有来头的。远的如买下严家花园的木渎首富严国馨暂且不说,只是近代,出自严家的达官贵人即不可胜数。如生于木渎、少时曾就读于木渎小学的严家淦(1905-1993),名静波,49年离开大陆后曾官至台湾政府财长。严宝礼(1900-1960年),生前曾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上海赫赫有名的《文汇报》的创始人。等等等等。究竟是木渎的地气使人上进,还是严氏治家有方,我辈无从考察,只有临园羡人的感慨了。
出了严家花园,倏然间受到阵雨袭扰,兼之在木渎继续游览其他景点的时间无多,只得恋恋不舍,登车而去,奔赴同里。行车途中,余与内人闲谈,忽然明白,虽然跟随旅行团会使旅程降低成本,同时增添许多方便,但也无疑要以旅行的自由作为牺牲来予以交换的。譬如游木渎,便无法尽兴畅游榜眼府第,这实在有些患得患失的可惜。因为对于旅游来说,对所到的地方了解的越多,游览时所引起的联想便越多,由此而获得的快意便越高涨,部分地失去旅行的自由,无疑会使那种因旅行而带来的快感大打折扣。这实在是旅游心理学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随着巴士的颠簸,我闭目细思,我猜测着,木渎人之所以在严家花园的旁边再立一个榜眼府第的牌子招揽游客,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在这个古镇的科举历史上,所产出的最高的学历就是榜眼吧。如果论及科举取得功名人数的多寡、级别的高低,恐怕木渎以其最高榜眼、进士20人、举人27人的战绩,还是难以与其附近的同里相比,因为毕竟同里出过一个状元、进士42人、文武举人90余人。但论及两地人物在世人眼里的地位,两者还是在伯仲之间。据当地人所提供的谈资,两镇历代以来人才辈出,如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就是木渎人,而清代以来木渎还有诗人、诗论家沈德潜、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冯桂芬等人,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人物。至于同里,除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去病外,则有著名的金松岑——这个人对于很多现在的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如果提及柳亚子、费孝通、潘光旦等人,人们似乎应该知道。而这些或是大诗人、或是大学问家的由来,竟然全应拜金氏所赐,这些人全部是同里人,并且全是金松岑老先生的门下学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江浙一带,自古才人不断,吾见之矣!
古代的先贤们曾说,孔子登蒙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余之苏州一行得之矣。不下江浙,不得见东吴之风流名士,不到曲阜,难以明圣贤之道。名士间内心岂有灵犀也?盖诗书永住心间,以作为传承之纽带也、为人为学之标准也。而今见苏州名士,莫不知书答礼,忠君爱民之辈,更倍感我国学之博大精深。忽然想起苏州名士潘祖荫旧事,感慨万端。
潘祖荫是苏州吴江县人,至于究竟是木渎还是同里人,因游览的时间过短无暇细细考究,只知其为清朝咸丰二年的探花。此公精于赏玩古玩,并因识别古玩而兼具识人之禀赋,真是奇才,曾与后来的光绪帝师翁同和并称少年才子,有翁、潘美誉。咸丰年间,老潘任朝廷南书房侍读学士,因当时的名幕左宗棠被参“劣幕”,老潘却不住左宗棠的亲家郭嵩焘的鼻烟壶的诱惑,慨然提笔为左师爷上了一道保奏折,与曾国藩、胡林翼、王恺运等人共同组成保左同盟队并自任先锋。老潘保左宗棠的奏折中除了大肆吹捧左爷之外,还尤其做了一个千古名句为总结,云“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当真令湘阴人大张其脸,老左也从此踏上了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老潘因此洋洋得意,并坦然笑纳了郭嵩焘奉上的润笔费纹银三百两,而保左佳话后来在学界和士林也一时被传为美谈。
嗟夫!
同里。
至同里时,那江南的细雨下得正爽。余屏弃了雨伞,独自在细雨中领略江南雨润物细无声的意境。众驴友随导游自同里刘家弄进入明清街,余与内人亦随之。雨中赏明清街、乌金桥、泰来桥、鱼行桥、南园茶社、穿心弄,为内人购买蓝印花布衣裙一套,并与众驴友共同乘舟访水上人家。真人生之一大惬意事也。
余之游览江南古镇的念头,全部起因于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似水年华》所致。黄磊先生和刘若英小姐演绎出来的古镇风情,倾倒了我和内人,而实地踏访古镇的渴念竟然不可遏止,最后竟干脆买了一套碟版做为收藏。四月天里,则更加南方一游一览实地矣。实在地说,这种因一部电视剧而作为旅游动因的事情,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但此行亦若有憾矣,皆因同里虽然也是影视城,但毕竟不是《似水年华》的实景拍摄地浙江之乌镇。
及至真正在雨中踏上江南水乡的青石板路,才知要了解水乡情境,非亲自走上一遍不可,任何书本子上的知识都是徒然。身处在渔家的小舟之上,耳闻桨声荡荡,吱吱纽纽的摇橹声搅动起碧玉也似的一片春水,伴随着晰晰呖呖的雨滴声,灰蒙蒙的天光映照得皱起涟漪的河面上一片青色,与那梦中关于江南的无限想象联系起来,真当得起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称赞。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吟咏江南时,用“风景旧曾谙”句,现在回顾起来,才知道只有置身水乡,这“旧曾”两个字用的大诗人手笔才能够体会出来。设若未曾到过江南而首次目睹江南风光者,是断然不会感受到江南之美的。因为这江南的风物只应用来细品,而走马观花地浏览一圈,无论如何是难以领略其韵致的。
据当地史料记载,同里旧称“富土”,唐朝初年因其名太侈,改为“铜里”。到了宋代,便有文人将旧名“富土”两字相叠,上去点,中横断,拆字为“同里”,沿用至今。同里位于周庄西面10公里处,距苏州城只18公里,四面环水,镶嵌于同里、九里、叶泽、南星、庞山五湖之中。建筑依水而立,有“东方小威尼斯”之称。顾名思义,同里的主要特色是水多、桥多。与木渎和乌镇一样,同里的明清建筑也很多,所以,在其主要的观光区明清街的道口起始门楼处,即使费孝通老先生题写的那“明清遗风”的四个大字,竟也道不尽其历史容颜。
穿心弄。
同里的豪阔士绅、名门望族俯首皆是,以至于屋宇稠密,风格古朴、意境深沉。粉墙黛瓦的深宅大院间,则似乎于偶然之中造就出曲径通幽的条条弄堂。余独爱明清街侧的穿心弄。在同里鱼行街的穿心弄,我与内人踏雨牵手而行。弄内绵延,曲折宛转,直至三百余米,而最窄处仅有半米,只容一人过。脚下石板空空有声,细看时,石板下竟全是悬空,踏之悠然,即有空灵朴拙之音。行至穿心弄尽头,蓦然回首时,赫然见一对年轻男女学子,如同情侣模样,在弄内互相拥护,深情亲吻,余与内人会心一笑,顿觉温馨无限,而心亦忽然见苍老,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忽然记起古语有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余与内子相视而笑,眼底竟不由湿润。执手相看泪眼,一时竟无语凝咽。
走在同里的那些闪烁着江南雨滴水光的青石板路上,有时候思绪猛然会在一刹那间变得恍惚迷离,犹如梦中。余留恋于因江南水乡而产生的一种难以言说情绪里。同里的建筑依然,舟船依然,碧水依然,人群依然。而在苏州,在同里,在木渎,是什么让人心中涌起近似颓废的陶醉?我在想,也许建筑和景物本身并不是一个地方最主要的景观,而那些最重要的、被称为主角的,却恰恰是最易被人们忽视的沉淀于建筑和风光之上的时间。时间的因素被无数次地为人们所观照,它不动声色地穿梭于同里与木渎、苏州这些比明清时代更早的青砖、黑瓦、小桥、细柳之间,而这些早已历经时间磨练的沉淀,恰恰是浮躁的现代人那所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所无法具备的。此时,当我们把内心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历史的面前,并默默地与回荡在南方水乡的先贤们的灵魂进行对话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内心也会因此而脱离现世生活的困扰,并由此而获得了解脱的平静。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就在我们淋着这江南的雨滴的时候,这些雨滴本身也具备了南方水乡的历史沉淀和人文内涵呢?
是夜,车行80公里,近5时许至上海。夜宿上海普陀区之北海宾馆。晚宴后乘车冒雨游上海外滩夜景。
5月4日,上海。天气晴。游上海外滩。游上海繁华街区之南京路步行街。游上海老城区之城隍庙。午餐于城隍庙小吃街品味蟹黄小笼包、烧卖、广式蒸蛋、贵州咸肉炒饭,几几乎吞下舌头酿出肉体伤害。午餐后乘车游上海陆家嘴金融区、浦东新区。下午四时整一众驴友乘车返青。
同游者:青岛新闻网之网友绒毛小球,胡同里的猫等,领队鬼娃娃蓝瞳等,余之忘年交郑老师夫妇及同行者诸人45。途中购书十与册,曰:“苏州史迹”,“小桥烟雨之乌镇”,“花样年华之香港”,“庄子通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