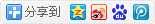苏州的婚纱和上海的姑娘们
苏州和上海都像是这次旅行的插曲,事实上,所有的旅行都有插曲:遇到的人、听到的话、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甚至错过的人和车、浪费的钱与最终失望的期待等等等等。
苏州和上海我都来过,都好几年了吧,每次来见到的人都不同,目的也不同,对于我,来苏州和上海旅行的目的已经非常淡了。
苏州当然是要买婚纱——一句“当然”就把什么都弄成这么理所应当,而事实上,就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老公才非常惭愧地对我说:“我妈这五一有事,我们不能回去办婚礼了,她怕你不高兴,让我好好跟你说。”
我突然眼前一亮,惊叫着说:“真的吗?真的吗?那我就可以答应朋友一起去阿拉善了。”
可怜的非一狼同学无比郁闷地说:“我妈真是没看到你这个表情,哎,她还怕你不高兴呢。”
其实,去年的两个黄金周我都抛弃老公和别人出去玩了,行程大概都有一个月,其中一次还是用婚假。我对于婚礼的态度就是可办可不办,但婆婆喜欢热闹,我也愿意让她老人家高兴,所以我开始就拒绝了和老朋友塔拉回她的阿拉善老家。
塔拉,在蒙语中是大草原的意思,她也是我唯一认识的蒙族女孩,她的普通话极其标准,闭着眼睛听她讲电话,很是温柔动人。
不过我现在还没在阿拉善,我在温暖的东部,我和同走新疆的上海妞VICKY一起走在苏州。4月5日是清明,很多上海人回苏州老家上坟,车票不好买,VICKY就一早替我们买好了。
苏州,我曾经一个人来过的地方,当时我坐船到寒山寺,水非常脏,但浸泡在水里的房子让我印象深刻,觉得如果水是美的,那么那段水路该是要大大加分的,可惜不是,也就有了我的遗憾与缺失。
可是,今天的苏州我是那么陌生,VICKY更多年没来过了,她比我还陌生,我们一路对话“我怎么记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拙政园漂亮吧”“寒山寺怎么这样啦”诸如此类。
还好,我的目的是来买婚纱,暂时不办婚礼,可是如果要办,我还是要准备婚纱,今天已经这么近,就索性先买好放那,我就不必特地来这了。
因为缺乏逛街的耐心,我只转了两家店,试了三件就确定了一件,只是尺寸有些大,店家要给我改动,我们就利用等待的时间去了留园和枫桥,晶晶还和我老妈去了寒山寺。
真的变化太大了,我对苏州无比陌生。我去甘肃青海四川时的同伴小遇是苏州人,我曾问他:“你们去园林是否如吃萝卜白菜那样容易,不买票的吧?”他当时白我一眼,跟我解释了一番。小遇讲苏州话真是温柔,同行的常州女孩糖糖就一直笑苏州男人讲本地话也非常“糯”。
其实留园是我很想来的,因为我以前来苏州的时候没来这里,当时就想,下次要来,这一个下次,就不知道几年过去了。
留园是以静观为主的园林,拙政园刚相反,它是动观为主静观为辅。我记得我以前去拙政园,就听朋友说起要“移步换景”。
留园是与拙政园齐名的中国四大园林之一,但是不断的修整令其完全失去了最初的味道。所以我想,不能说它不好吧,只能说它现在不好了。古人在修建园林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花园的树是什么品种,种几株花草,门要冲哪开,窗户要几扇等等,可是我们已经不能更好地体会生活的艺术了,我们开始懂得去掌握“生活的经济”,同林语堂先生向外国人推销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年代已经相去甚远。
可是你又不能说国人不对,搞经济当然没错,只是失去的也太多。我路上和老妈聊起过数次,毕竟艺术是不可再生的,它存在人的脑子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代代相传里,一旦人不再了,艺术也会消失,就好象这么多年也不过出了一个毕加索,是的,你还有达利,但他是达利,达利和毕加索是两个人。
而且从前是一个人教很少的学生,现在,一个班级几十个人,怎么相同?老妈经历过那个年代,虽然没有印上很深的烙印,但毕竟经历过,体会更加深刻。她总是叹气,颇多感慨。
我喜欢枫桥里的海棠糕,大家人手一只海棠糕,只有我不过瘾,又去买了两只。没办法,我就是无可救药地喜欢江浙、闽粤一带的饮食。
当年去福建的时候,我时常哭,也许因为年轻,但是的确不适应气候。后来不哭了,可是也不快乐,直到日后我离开,我才开始怀念那里的食物。原来人在当下的时候未必懂得珍惜,当时年轻,不大懂得。也知道很多经历在日后才能成为财富,但“现在时”不是“过去时”,其实完全没可比性,因为苦痛是在过去以后才变得没有份量。
我和VICKY聊天等待晶晶和老妈去寒山寺。太阳温暖地照下来,我俩聊起过去了的新疆和即将开始的阿拉善。
然后她俩出来,我们就去拿婚纱,VICKY说她可以把她结婚时的项链借我用,我说好,婚礼就是要“一点旧一点新一点借来一点蓝”,随后补充“今年未必有时间去办啦”。反正买那放着吧,我的体重六年来没有一点变化,所以就不算浪费。
傍晚就回了上海,在新客站附近吃小火锅,上海代表团的是米拉拉、格格和flyingfish,当然还有请客的VICKY,地点是米拉拉选的,是方便我们吃完坐火车。
格格是第一次见我,她说我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同照片也有很大区别,是,一般都这么说;VICKY和米拉拉用上海话狂聊,我们三个北方人完全听不懂;飞鱼来的最晚,一见她,晶晶就悄悄告诉我:我觉得她是长得最像上海女孩的,我也赞同,飞鱼五官不是很漂亮,可是样子就是很美。
米拉拉是阿里猪以前同走甘南的同伴,格格同猪也很熟,大家就妄图说猪的坏话,但最后,想到他是一个臭男人,就失去了说的兴趣,草草几句收尾,还害地广东那边的阿里猪无比担心。可见猪不是好人,没有亏心事的猪永远不会担心。
相谈甚欢。格格提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当天的生日。我在火车上给她发短信,祝她生日快乐。她说没想到能见到我,我其实也是。
但自从有了莱特兄弟的伟大发明,就缩短了世界的距离。而自从有了大规模的人类旅行活动,就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后来我们和V、米、F挥手告别,在晚上十点踏上了开往洛阳的火车。只买到了两张卧铺,我就给她们坐了,我自己去了硬座车厢。
其实我无比痛恨坐火车,我至今都是更喜欢坐大巴,这实在是读书的时候坐伤了。后来一个人在北京和福建之间坐了几回硬座,更加害怕长途火车。
睡的很坏,不过总好过站着。有次半夜从徐州上车,没有座位,而车第二天晚上才到福建,我一想到漫长的夜要站着,我就无限悲痛啊——那时候非常年轻——我就在那哭,哭了会儿,想到眼泪无济于事,就擦干眼泪。第二天早晨,车到黄山,我才混到了一个座位。
人都是逼出来的,真是站着,也能活下去。但是累也是真累,谁都不是钢筋铁骨。
第二天上午十点火车到达开封。这时候离我上车已经十小时了,早晨火车有了卧铺,不过我也不想补,反正中午就能到洛阳。
开封上来了几个人,一看便知道是农村的,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女孩子。说是孩子,其实也总有十几岁吧,并不漂亮,有些龅牙。火车开动的一瞬间,她突然就哭了,没有大的声响,可是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来。
其中一个带她一起来的长辈问:“舍不得?”她点点头,继续哭。大人听完也没理会,两位阿姨自己聊起天来。
女孩子就坐我对面,我抬眼能看到她黑乎乎的小手正用一块脏兮兮的小布擦脸上的泪,她居然一直在哭,表情那么悲伤。
我想起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是宿舍第一个离开的,又是从哈尔滨去了几千公里以外的福建,她们七个就来送我。在火车即将开动的一刹那,我突然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像开了水闸。
别离和泪水总有不同的原因,但情绪的表达总是同样真切。我没同她说话,一个人想哭的时候,总是害怕别人的安慰与询问。
我抬头看看她的脸,很清楚地知道,这里已经离上海越来越远了。而洛阳,洛阳该是另一种面孔和表情。
20060407 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