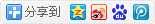有一种悲痛叫“永别”,那是和至亲的人在这个尘世的分别,即使再见,也必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那是撕心裂肺的哀恸!
可是,居然还有比那更加悲哀的,那是“慢慢的永别”!
我的故乡是北京——她是曾经的边地,自元建大都便有了其下八百年帝都的荣耀。1422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于是一座巍峨壮丽、傲视寰宇的伟大帝都便横亘在这北国。她拥有无与伦比的气魄,是世界上唯一从一开始就是规划出的巨大城市。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几十里由南至北,依次排开布局,无数门、楼、牌坊、玉桥,跌宕起伏……中轴线东西对称分布的是南北东西横平竖直的马路、一幢幢四合院构筑了一条条幽静的胡同,古树新木在其间伸出枝丫,四时景致个不同:春天的柳絮、夏天的枣花、秋天的杨毛虫、冬天漫天的飞雪……越过每一座屋脊都仿佛看到传统文人画的中“风人咏空谷”的意境;分布于者美妙民居建筑之中的是或雄伟、或玲珑的宝塔、楼阁,那是庙宇、王府,是书院、衙门……环抱着这美丽图卷的是那座巍峨的城池。
北京城分南北两块,曰内城、外城,有城门内九外七座。每座城门都有箭楼、门楼,其间是瓮城。绵延近百公里的城墙,高大、敦厚,每隔八丈就有向外突出的墩台,用以增强防御功能……
就是这座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伟大城墙,经历了六百年的风霜雨雪,以他的胸膛抵御了无数次外敌的入侵,无论是李自成、皇太极、八国联军、日本鬼子,都没有能打断这以中华民族坚强意志和勤劳勇敢筑起的城墙,仅仅在五十年前还巍然屹立的城,终于在毛泽东的一声号令下被彻底拆除!!如今,只有正阳门箭楼、门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连带的一段不足三里的残破城墙幸存。这,是无声的控诉!……
今天的二环路,就是那座内城城墙的坟冢。每天乘车跑在上面,我似乎总能感到那城池的灵魂用一双充满幽怨、凄怆的眼睛从天上凝视着我们,仿佛在诉说她六百年的沧桑、质问后人的无情。
当五十多年前,北京人民以他们传统帝都人的质朴、宽厚、天真夹道欢迎那支入城队伍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欢迎来的是这座城市的毁灭!!仅仅七年后,这座无与伦比的伟大城池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即使日本鬼子都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却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城池既然没了,这个城市的风物和她的人民的命运就几乎是可以预知的了: 于是,无论是元朝的双塔,还是清朝的王府、大小寺庙、道观、牌楼被飞快地清除…… 即使是“中华门”也马上夷为平地!
那象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皇家建筑成为了封建皇权的象征,于是社稷坛变成了中山公园、太庙变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斗转星移又是五十年,当皇家建筑,除了紫禁城外,被破坏殆尽后,失去节制的资本又与权力结合,以空前的速度、力量吞噬北京的民居。大片大片的传统街区被以“旧房改造”的名义推平,曾经幽静、雍容、敦厚的四合院、胡同眨眼间变成平地,又在眨眼间变成数十层的钢筋铁骨的大楼。那些世代过惯了胡同中闲适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的居民,被以“搬出危险房,再园安居梦”的口号标语永远赶出了城区……
充满同年欢声笑语的、用以捉迷藏的胡同,无论多少曲折回转,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都不会迷失;而今,为汽车腾出的空旷的马路、高耸的水泥大楼才使我们迷失。
胡同的消失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消失。一个地方自身的定义靠的一是建筑、二是民俗。当二者都消失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不变的只是地理坐标。
可悲呀,北京就每天以这种方式消失——太多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土著,都应经只能靠坐标辨认了!
每天,一片一片的平房被推倒,北京就像被凌迟一样地死去。
我们每天都在与我们可亲可爱的中华故都说“永别”,这正是慢慢的永别。
在心里哀恸的,又岂应只是我们这些曾经的天子脚下的臣民?难道不应是这中华故都曾经带给荣耀的所有炎黄子孙?

(内城西北角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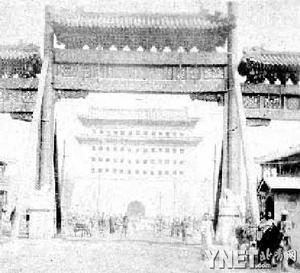
(正阳门五牌楼)

(正阳门俯瞰)